近期,上海外滩历史保护建筑三菱洋行旧址外墙被野蛮涂刷,反映的是历史建筑保护法规执行不力和违法者对法规漠视的严重程度。苏州河边裕通面粉厂旧楼被市民举报,有关管理部门才出面解释,这是正在保护性拆除。日前,位于杨浦区的保护建筑英商班达蛋行又被夷为平地。如果这些拆除行为都经过专家论证和规划部门批准,那么,属于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可移动的建筑,其专家论证结论和规划部门批准意见,是否在开工前就该向公众发布?既然属于保护建筑,就具有公共属性,当然就包含着公众的知情权;其次,公示应该在规划部门批准之前,公示才有实际意义,因为,公众有权质疑专家论证结果的合理性和代表性,同样,公众也有权质疑规划部门使用权力是否正当。
如果今天还停留在对稀缺历史资源机械式保护水平上,那绝对是城市管理上的悲哀。表面上看,三菱洋行旧址外立面被野蛮涂刷,是破坏了老建筑的外立面,触犯了历史建筑保护法,只需要严格执法就行。但更深层次的却是,野蛮涂刷破坏的是外滩整个建筑群的历史秩序。历史建筑秩序由建筑风格、使用材料、建筑色彩以及与其他建筑的关系构成,与周边的环境相协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建筑秩序,就包含了原生态的生活元素,并形成了公众的历史记忆,建构了一个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美学认知。
当世界已经普遍从静态单体保护向动态活性和区域保护转型之时,历史建筑秩序保护其实还是简单的,只需要严格立法和执法而已。更具挑战性的是,如何把历史建筑资源纳入城市改造重建的过程之中,把旧区改造和周边的历史资源形成有机联系,让历史建筑资源活化,使文化价值放大并有效溢出,为建构有价值的新建筑秩序提供内在的文化支撑,才是一个城市管理水平体现的标志。无疑,在世界城市化的潮流中,对每个城市来说,历史资源都是恒定的,不可再生。因此,考验一个城市管理水平的核心质素,就是如何在城市改造重建中,能继承并发展城区已有的历史建筑资源,作出有效的建筑文化价值延伸,构建新的片区建筑秩序和文化价值,这也许就是城市改造重建水平升级的重要途径。
被誉为新加坡城市规划设计师的刘太格,对规划和建筑秩序曾有个形象的描述,他认为,在一个区域和一群建筑中,其关系就像一个大型交响乐队,应该先设立首席建筑体,其他建筑应与其保持从属关系和协调关系,而这些建筑虽然在体量或形态上有从属关系,但建立的确是一个整体的建筑秩序下的个性补充,这才会有协调性和观赏性,就像交响乐团虽然有首席小提琴手,但丝毫没有掩盖其他提琴手的演奏价值。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现在的城区重建的状况,宽容一点看,不少建筑单体还是能接受的,但整体一看,不少建筑张牙舞爪,都想做老大的气势,建立的是冲突、矛盾、突兀、不协调,严重破坏了城区建筑秩序感,何来城市建筑美学的建构?这也就是我们目前大部分城市改造和重建后,最让世人诟病的突出问题。
多年前,杭州西湖申遗的最大障碍,表面看是西湖四周混乱的天际线过不了评委关,其实是大量新建筑完全突破了西湖整体的美学形态,不但破坏了西湖原来的历史协调性,而且与历史景观形成强烈发冲突和不协调所致。建筑之间是断裂、冲突的,新建筑秩序没有建立。反之,在许多成功的改造案例中,都把城市历史建筑和历史资源作为改造定位的基础和出发点,并由此建立改造方案和基本策略,如众人皆知的德国的鲁尔老工业区改造和英国的泰晤士河边的泰德当代美术馆,都是充分利用历史建筑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价值,不但让历史建筑使用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更是形成了新的区域价值和建筑新秩序。日本箱根雕塑公园,充分利用了著名雕塑大师摩尔的艺术精品,与山林的地势地貌有机整合,使这片本来很平常的山岭,成为一个世界级重要的区域文化的特定场所,人们就记住了箱根。它所做的其实就是把艺术资源与自然山貌做了有机的整合,形成了艺术与山林之间的秩序感。即使被人诟病的上海新天地,它能变腐朽为神奇,也是一种历史资源延伸并放大的产物,新天地有效嫁接了几步之遥的淮海中路的商业地标资源,让淮海路上留存的都市商业精神和消费文化顺利溢出,新天地的外壳装入的是淮海路的内容和精神,新天地不但获得了商业活力,也就获得了文化活力。
显然,当一个区域性旧区改造开始前,应该充分了解和仔细调查该地区的历史资源状况,尤其是典型或重要的历史建筑和文化资源以及周边分布状态,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规划旧区改造的思路,使其文化效应最优化,最终也更能使经济效益最大化。
最近,上海苏州河边曹家村旧区改造,公布的改造建设方案,仍然是一个平庸的方案。作为上海重要的景观河道,苏州河流经上海市区段形成不少河湾,但流经这儿形成S 形河道,连拐两个弯勾勒出一个大S形状,怀抱了两个半岛,历史上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学院)就占据了河南岸一个半岛。另一个河北岸半岛就是与圣约翰大学隔河相望的棚户区曹家村。从远处看,圣约翰大学整个校园铺开贴着河面延伸,河面托起绿色葱郁中隐隐约约的暗红色建筑群,形成了良好的建筑秩序感。曾有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上海开埠以来,“洋”、“商”、“女性”共同在这交织成一个新的文化秩序。直到今天,圣约翰古老的塔钟每天按时响起,在晨晖和暮色中,随着清风远远飘扬,挥洒着浓浓的古意和诗情。这种文化秩序和建筑秩序之间建构的虚实相间的历史关系,以一种独特的建筑意向和秩序感,留存至今。而隔河相望的曹家村改造,如果在规划和设计之前,能好好想一想,如何利用圣约翰完整而又有审美价值的历史建筑资源做足文章,能在功能、建筑形态、外立面色彩等整体与圣约翰建筑群形成内在呼应,不但能产生更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还会产生一个苏州河新地标。可惜的是,这个被称为苏州河边最后的黄金位置,就这样被廉价处理了。真不明白,规划部门为什么对一步之遥、独特的圣约翰历史建筑资源视而不见?最终,旧区改造结果只是多盖了几幢高层住宅楼,不但没能提升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价值,突兀的高楼,反而与圣约翰校园建筑形成冲突,影响甚至破坏了圣约翰校园所形成的历史建筑秩序。两岸建筑依然是各行其是对峙。与其如此,还不如一些艺术家们曾对着那片青瓦、破墙、斑驳构成的一片棚户屋顶发出的感叹:屋顶上稀松的枯草,几度春来返青,秋去枯黄。常常掠过惊鸟和春来秋去的雁群,使得这片棚屋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因为这些破败的建筑元素至少还表达着地方和地域文化特色。
看来,大量历史建筑和历史景观在旧区改造和城市重建中,都会面临这样既尴尬又严峻的问题。既要保护历史建筑秩序,又要重建新的建筑秩序。首先需摆脱区域分割、各自为政的资源管理分离状态。除了立法和执法之外,还要资源和管理上的整合,由于各个区域经济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水平的差异,形成落差之外,还会造成区域性断裂,不但是形式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断裂。增加建筑文化粘连性的前提是,要强化权威的、有高水准的规划设计和执法机构,同时,还需要执业规划师、设计师整体素质的有力呼应。上海市静安区近期对东斯文里老式石库门建筑群将实施整体性保护开发,利用旧的建筑文化资源,结合周边新的建筑和业态的协调性设计,体现了一种人文追求。令人值得期待的是,如果这片区域将来形成有价值的新建筑秩序,但价值的源头一定来自东斯文里。
今天,最令人担忧的是,时光在流逝,而我们仍然将面对更多蜂拥而出、杂乱无章的建筑,既让人无法亲近,更无法去命名和定义。故乡也将会成为一丝忧伤留在我们的仅有的记忆之中。
(作者:王国伟 同济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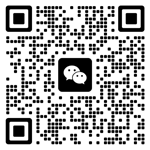

 BIM建筑网
BIM建筑网

